“死亡咖啡馆”分享经历仍能感受到那时冬日暖阳
上海手拉手生命关怀发展中心举办的死亡咖啡馆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獾并不害怕死亡,死亡只是意味着他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獾并不在意。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身体早已失去了控制。他只是担心他的朋友们会怎样。” “为了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巴杰告诉他们,很快有一天他就会走进那条长长的隧道,当那一天到来时,他希望他们不要太难过。”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活动室就像一个温室,有玻璃天花板和玻璃墙。 2020年8月19日,43岁的文静回忆起去年年底的这段分享经历,仍能感受到当时冬日温暖的阳光。 在十几位与会者的聆听下,她分享了英国画家Susan Wallet的图画书《獾的礼物》。
2019年7月,文静的父亲施先生在该院护理部的病床上平静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去世前,史先生带着文静参加了护理部组织的一场活动——同样是在这个“温室”里,医护人员、志愿者、患者和家属坐在一起,谈论死亡。
这种让参与者在舒适的氛围中讲述自己关于死亡的经历、知识和看法的活动形式被称为“死亡咖啡馆”。 2011年9月,英国人乔恩·安德伍德在他的家中组织了第一届“死亡咖啡馆”活动。 此后,死亡咖啡馆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迅速蔓延。 在乔恩·安德伍德的组织框架下,迄今已举办超过11,000场活动。
2014年,两位从事临终关怀领域的慈善家将死亡咖啡馆模式带到了中国。 特别是近三年来,医院、公益组织和个人开始组织和推广中国版的死亡咖啡馆。
父亲去世后,文静再次走进昆明市第三医院护理部举办的死亡咖啡馆,心中充满了思念和感激。 另一位参与者的父亲刚刚被诊断出癌症,眼中的痛苦投射到文静的心里,“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帮他解决什么问题,但我可以分享我走过的路。”
“单纯地谈论生与死,其实并不容易。但那个时候,在那种氛围里,你就会有一种共情的感觉。” 在分享《獾的礼物》时,文静意识到父亲也为自己留下了两件珍贵的礼物——乐观和勇气。 那一刻,文静为亲人的去世感到一丝欣慰。
在生命的尽头谈论死亡
文静第一次进入死亡咖啡馆时有些不情愿。 “我心里有一个疙瘩,因为看到‘死’字,我就不想去了。”
那是2019年6月底,80岁的石先生患有结肠癌,经过十个月的化疗后,决定转到昆明市第三医院护理部。 他告诉文静他喜欢这里。
“我们科室叫护理部,其实就是临终关怀,病人和家属来的时候,都是有(死亡)期待的。” 该科室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最早为老年患者和癌症患者提供姑息治疗的科室之一。 (姑息治疗)部门。 护士长薛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住进监护室的患者通常都是生存期不到6个月的患者。
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必须面对死亡。 如何与患者及家属谈论死亡,一直是困扰雪莲和她的同事的问题。
我们谈论或不谈论死亡有什么区别呢?
“临终前,病人可能想去某个地方,吃点东西,见见人,想想家人会为他做的事情,想要有机会向欠他的人道歉,向他所爱的人道别。但如果患者及其家属如果不接受死亡,不公开谈论死亡,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做。” 薛莲说,所谓临终关怀,就是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留遗憾,这一切的前提是让人们谈论死亡。
引导患者及家属接受死亡的生死教育贯穿于该科室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中。 死亡咖啡馆是他们尝试的一种生死教育形式。
2016年,昆明医学院护理学教授唐萍芬去瑞典交流,第一次听到外国同事介绍死亡咖啡馆。 “当时感觉有点奇怪,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谈论死亡总是有点不吉利。”
回国后,唐萍芬仔细思考,发现忌讳死亡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 “鼓励人们在轻松舒适的场合打破死亡禁忌,在中国也可以尝试。”
2017年12月,唐萍芬指导昆明市第三医院护理部开展死亡咖啡馆第一期活动。 当时,关于死亡和遗忘的动画片《寻梦环游记》上映,唐萍芬用它来预热节目。 “我们(医务人员)也有想念的人,平时没有机会表达内心的感受。那天我们都说出了自己的秘密,很伤心,但也很解放。”

第一期成功后,昆明市第三医院护理部大约每月举办一次死亡咖啡馆活动。 活动信息会提前张贴在病房内,患者及家属可以报名参与。 石先生邀请女儿参加第18届死亡咖啡馆活动。
“你先去吧,我很忙。” 文静婉拒了一次,但活动当天,她还是有些担心,就悄悄跟着父亲去了活动室。 站在“温室”门外,文静向主办方解释,如果她在场,父亲可能就说不出话来。
那天唐萍芬也在场,石先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过去了,她还记得这个“非常非常帅的老男人”说起自己的过去。 他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对生活非常追求,他一直在规划未来。 书籍,还有更多讲座。”
当被主办方拉进活动室时,文静听到父亲刚刚分享完自己的生活,然后郑重地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他非常感谢自己的女儿。 “之前他在我面前表达不多,但那天他说了很多。”
一个月后,石先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最后一次共度时光里,父女俩就死亡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施先生不想通过过度治疗或插管来延长生命。
当施先生呼吸急促,护士问他要不要去ICU时,文静选择了尊重父亲的意愿。 她握着父亲微肿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天堂是最美丽的地方,别害怕。”
文静相信父亲安详地去世了。
生死观的碰撞
文静是上海的一名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讲师,经典的生死教育绘本《獾的礼物》已经在她的知识库里了。 但父亲去世后,文静发现自己真正理解了这个故事。
故事中,獾的死亡被描述为沿着一条长长的隧道奔跑,所有因獾的死而悲伤的动物们在回忆獾教给他们的事情时,慢慢地融化在悲伤中。 獾教鼹鼠如何剪纸,教青蛙如何滑冰,教狐狸如何打领带……这是獾留给他们可以永远珍藏的离别礼物。
再次参加死亡咖啡馆后,文静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她是一个经历过的人,她希望能为其他仍然被死亡阴影所困扰的参与者提供一些帮助。 她决定分享《獾的礼物》,这是她希望传达的一种关于生与死的观点。
在死亡咖啡馆里,不同的生死观常常发生碰撞。 一些参与者纯粹是为了分享,而另一些参与者则试图发出求助信号。
“如果死亡只是离去,我为何如此悲伤?” 2020年8月16日下午,杭州西湖畔的一家咖啡馆里,一场向公众开放、招募参与者的死亡咖啡馆活动正在进行中。 一名陈姓中年妇女说话时哽咽了。 一年前她经历了父母的去世,至今仍无法释怀:“我无法接受他们走了。如果他们走了,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想活到几岁?” 活动负责人(即主持人)用轻松的语气问道,以化解紧张的气氛。
“我身体还不错,不出意外的话,85岁的时候我肯定还在。” 中年妇女的声音也变得轻松了一些。
“那你还有几十年的寿命。” 领导也没有过多劝说我。
这家死亡咖啡馆由上海手拉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手拉手”)主办,由该组织创始人黄卫平领导。 手拉手协会成立于2008年5月,据该组织介绍,它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致力于临终关怀的非营利组织。
2014年,手拉手的另一位创始人王莹在德国留学,结识了同组的翻译黄子仪。 两人聊起临终关怀的死亡咖啡馆,决定回国后在大陆开展这项活动。 当时,黄子怡在北京以“死亡茶馆”为名,王莹在上海以“死亡咖啡馆”为名组织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讨论死亡的沙龙。 但此后,死亡咖啡馆在国内沉寂了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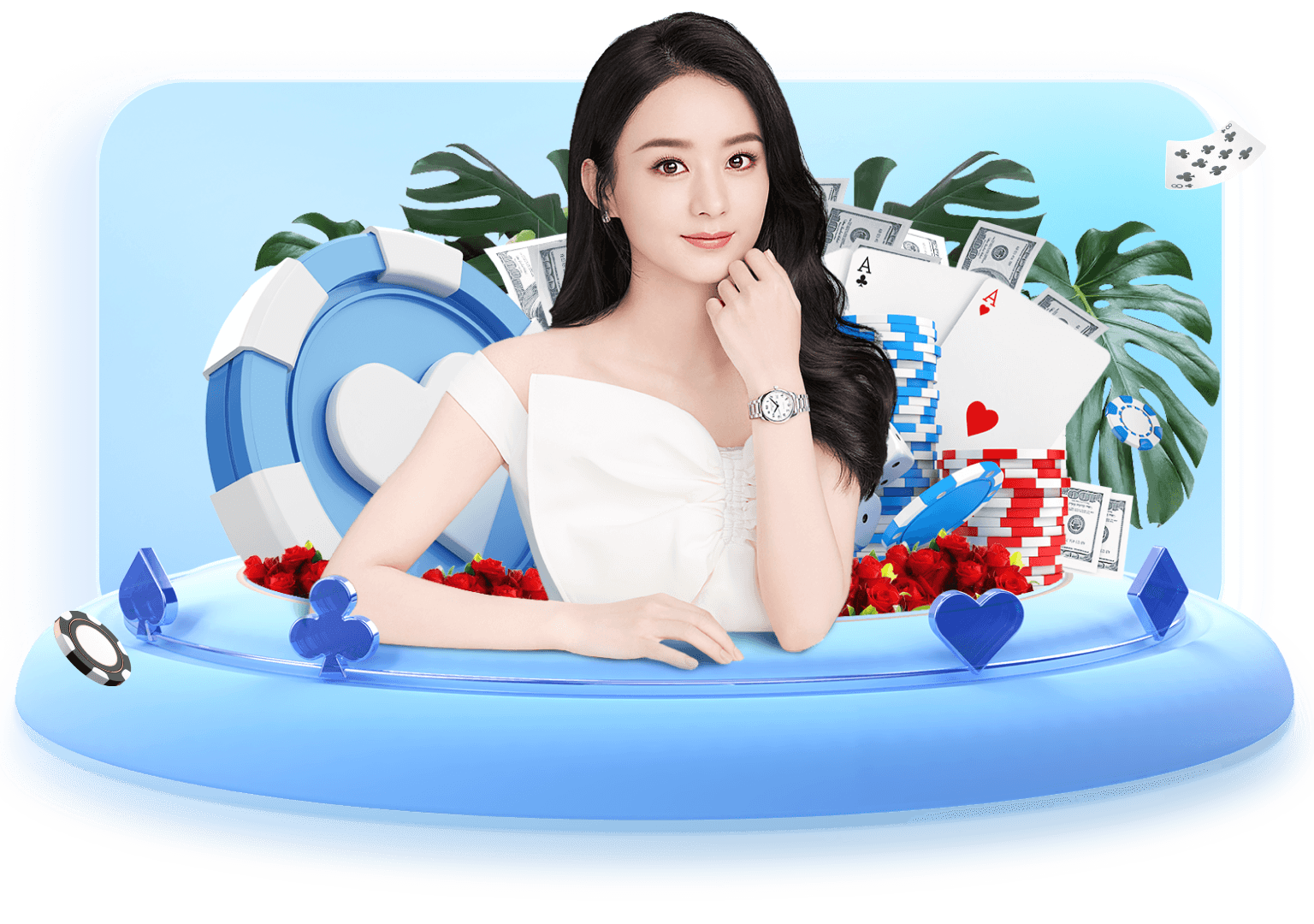
“那段时间,我们专注于经营叫醒死亡体验馆。” 2016年4月4日,历时4年、投资400万、门票444元/人的全国首家4D死亡体验馆开业。 在上海开业,三年后关闭。 黄卫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死亡体验中心的运营成本太高,“只能等人来”,无法满足手拉手在全国推广生死教育的需求。
唤醒死亡体验中心关闭后,王英和黄卫平转身决定以更灵活的业态和更低的运营成本推广死亡咖啡馆。 他们先后在西安、长春等地开展活动,培养能够在当地组织死亡咖啡馆的伙伴和带头人。 2020年8月,手拉手重启了因COVID-19疫情而暂停的促销计划。 第一站是杭州,9月是上海、镇江,10月是广州、成都。
8月16日下午,浙江萧山医院管理人员杨丽丽看到“死亡咖啡馆”活动的信息后,立即报名,花费44元。 她不仅报名了,还拉拢了医院的一名精神科护士和一名重症监护室护士。 “杭州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活动,大家都有些兴趣。”
杨丽丽认为,一个人如何理解死亡,会影响他如何做出人生的决定。
三四年前,杨丽丽在上海参加了一次“死亡演习”。 她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人就是女儿,但在模拟死亡的那一刻,她关心的却只有母亲。 “因为我坚信我的女儿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 此后,杨丽丽对女儿更加信任,与母亲也更加亲近。
此次参加死亡咖啡馆,杨丽丽希望了解其他人如何探索生命、理解死亡。 她形容这段经历“弥足珍贵”:“十几个陌生人讨论死亡,但他们并不感到害怕。就连说生命毫无意义的陈姐,也向我们讲述了她连跟丈夫说话都无法说话的感受。”诚实地请求帮助也很有价值。”
杨丽丽说,在死亡咖啡馆,参与者会尽量不去评判别人对生死的看法,“但这种碰撞本身就很有价值”。
“这不是心理咨询,也不是丧亲咨询。”
黄维平主持过数十场“死亡咖啡馆”活动,也面对过很多像陈姐一样沉浸在丧亲之痛中的参与者。 当这些参与者分享自己的经历时,黄卫平感觉到他们希望得到领导的帮助。
“但我不会刻意去满足这个期望。” 在黄卫平的理解中,领导者和参与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领导者只是为参与者创造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场域,会有必要的引导和回应,甚至尖锐的问题发生碰撞,但并没有比参与者更多地掌握所谓的真相。 “谁敢说自己是面对死亡的专家?”
在向公众发布的活动信息中,手拉手明确表示,死亡咖啡馆“不是心理咨询,不是丧亲辅导,也不是心灵鸡汤或所谓的正能量,也不保证您来了之后就会很开心。”
赵小白在北京经营一家钢琴培训工作室。 2019年参加“手拉手”推广计划后,他开始在工作之余担任领导。 在COVID-19流行之前,频率是每两周一次。
向赵小白求助的参与者并不多。 当他们见面时,他并没有给自己施加任何说服的压力。
“我相信他已经听到了我能给的建议。如果他能出来,他早就出来了。因为他不想出来,他只想沉浸在悲伤中。”失去亲人。” 赵小白认为,陷入痛苦是个人的选择,因为感受痛苦是生者与死者的联系。
死亡咖啡馆能提供的帮助,一方面是在谈论痛苦后情绪得到缓解,另一方面是听其他参与者描述类似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死亡是每个家庭都会经历的事情” ,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他不是唯一一个受苦的人。”
2019年初,赵小白病重。 躺在床上,他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回想起了自己的前世。 他一直被恐惧和焦虑所驱使,不为自己而活。
“病愈后,我看到‘死亡咖啡馆’三个字,立刻感受到了强烈的召唤。” 赵小白在2019年10月组织了第一届死亡咖啡馆活动,预约满额后,还有一位六岁的十几岁的老太太请求他包容——老太太很渴望分享一个她的濒死经历,她之前一直埋藏在心里,无法与他人谈论。
由于领导者并没有提前设定议程,也无意控制讨论的方向,所以每次死亡咖啡馆交流的焦点都会随着参与者的互动而改变。 也许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赵小白组织的第一家死亡咖啡馆里,他听到了几次超凡的濒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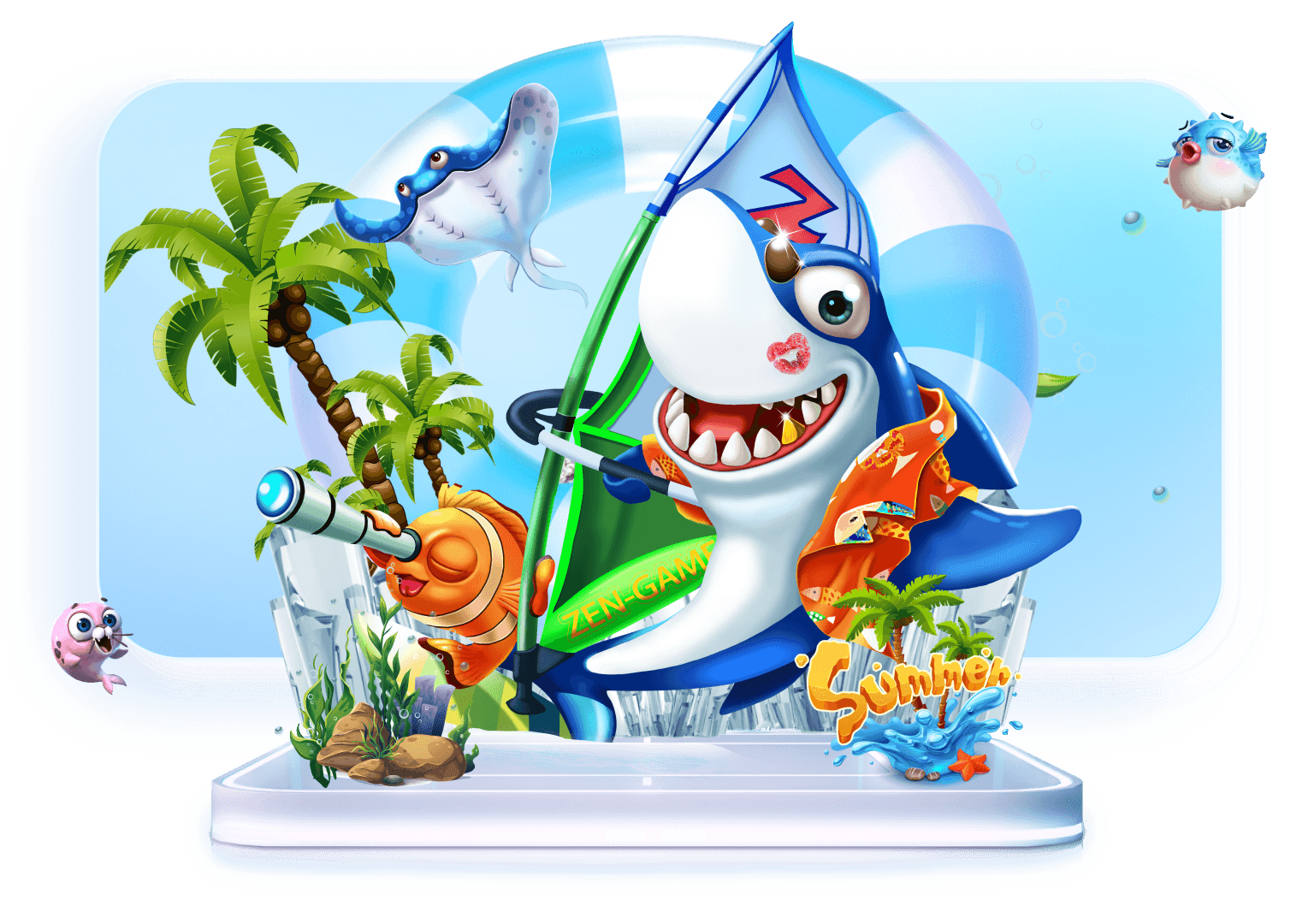
一位女士说,在手术台上,她有那么一瞬间感觉“灵魂离开了身体,就像脱掉了一件衣服一样,美丽又舒服”。 但她告诉自己,还不到死的时候,所以“灵魂回来了,但很不舒服,好像承受着重锤一样”。
“他们带来了生活中最不为人知的故事。” 作为组织者,赵小白觉得自己的收获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努力。 与死亡有关的故事让他越来越意识到生命的时间是有限的,死亡的来临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必须更加深情地生活”。
在上述杭州的死亡咖啡馆里,一位来自三级医院的麻醉师分享了他制定生前遗嘱的经历:两份放在了他的丈夫和他最信任的同事手中。 她希望,当自己有生命危险时,自己仍然有权根据事先签署的文件选择就医。
对于当天的很多参与者来说,医生的分享似乎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知识点。 领导者黄卫平趁势引入遗嘱监护,“和生前遗嘱一样,为了让人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死得更像一个人。”
国内外差异
李明久,80后,曾从事公益和跨文化教育工作。 2018年,他重返校园,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研究生学位。 在研究临终关怀和生死教育的过程中,他参加了许多死亡咖啡馆的活动,有些是在医院内举办的,有些是面向公众的。
李明久对比了一下,发现医院背景的死亡咖啡馆承担了部分治愈功能。 “患者家属谈论死亡可以起到舒缓作用。”
在向公众开放的死亡咖啡馆中,参与者大多是女性和年轻人。 “活动尽可能营造一个开放、安全、支持的氛围,目的是减少大家对死亡禁忌的抵制。但很难说这种改变是否会影响到更多人。因为那些报名参加的人参加活动的人可能自己就准备好谈论死亡吧。”
从研究死亡教育转向关注死亡咖啡馆,对李明九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生死教育的缺失,但很少有人提出生死教育应该如何进行、采取什么形式。 学者们也倾向于从哲学或具体医学层面来研究死亡,而较少关注社会应用层面。 “这与国外形成鲜明对比。”
“国内外死亡咖啡馆的形式相似,但具体讨论的内容还是不同的。” 李明久举了一个例子。 在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临终关怀。 当当地人参加死亡咖啡馆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交流。 有关如何安排死亡的具体信息。 而国内参与者主要是分享对死亡的经历和看法,缺乏通过活动立法保障的资源支持。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四位死亡咖啡馆的外籍组织者发现,他们在活动中经常讨论与死亡安排相关的实际问题,比如埋葬方式、尸体处理方式、是否接受安乐死等。 话题甚至像是否可以采取绝食一样具体。 安乐死的方法。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退休教师萨拉·威廉姆斯(Sara Williams)从2014年7月开始,每月在自己的社区举办一次死亡咖啡馆。在她的死亡咖啡馆里,绿色葬礼、家庭葬礼、生前遗嘱等都是热门话题。
“我们在上次活动中谈到了墓地。” 萨拉·威廉姆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公园都关闭了,所以人们就去墓地寻找活动空间。
在国外,新冠病毒大流行对死亡咖啡馆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萨布丽娜·杨(Sabrina Young)在德克萨斯州坦普尔经营一家殡仪馆,大约四个月前,她开始每周四组织死亡咖啡馆。
“以前,我们通常在餐馆举办活动,那里提供咖啡和食物——这是举办死亡咖啡馆的标准。但疫情发生后,我们不得不改用Zoom(视频会议软件)。” 萨布丽娜·杨(Sabrina Young)说,当人们围坐在餐馆的桌子旁时,如果有人想表达同情,他实际上会伸出手,把手搭在分享者的肩膀上。 在网上,人们不再能够互相触摸进行互动,只能尝试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肢体语言。
同时,当参与者面对面时,谈论的内容往往只与生活圈子有关,“他们分享的只是天普城内的悲伤”。 如今,疫情带来的死亡恐惧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情感,而Sabrina Young组织的线上死亡咖啡馆也迎来了远道而来的参与者,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参与者。
“这场流行病使死亡咖啡馆从一个本地概念转变为一个广泛的概念。现在你必须尝试了解(来自远方的人)正在经历什么,而当你在餐馆里时则不必这样做。 ”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南方周末实习生 罗一凡


